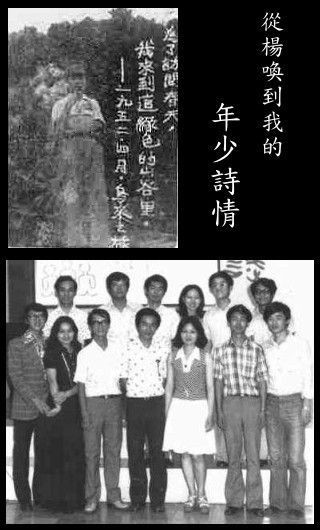
〈騎上白馬看看去〉
──從楊喚到我的年少詩情
1
楊喚在「童話裡的王國」中寫小弟弟是騎著白馬到童話王國裡去的。
而我是騎著白馬到詩的王國去的,迷上詩的我已是一名少年。
楊喚寫的詩作「二十四歲」形容二十四歲是白色小馬般的年齡。
我開始詩的創作才十七歲,應該是更幼小的白馬。
白馬,像雪似的,降臨在我的腦裡。
牠隨著我的思想行走;跟著我的感情奔馳。
牠,有時消失了。
我開始想以一條繩索繫住牠。
我編織繩索,用語言,用繪畫,用音樂。
最後,我選擇了用文字。
2
我用文字編織了繩索,一端繫著白馬,一端繫著我的青春歲月。
從臨海的小鎮翻越大肚山而來,將白馬繫於台中盆地。
當時,我遇見幾位同樣騎著白馬的年紀相仿的青年,漫步於校園裡。
是的,我們自然而然的就聚合在一起了。
展開一場馳騁詩壇的約定!
一向認為自己是下墜星球的蕭文煌,以彗星之姿燃燒自己。
陳珠彬在晝與夜之間,以一棵藥菊之芒劃破非常茶色的毯。
莫渝啊,將沒人要的的成頓孤寂,說與孤寂聽。
呂錦堂畫圓成日,切弧為月,用馬蒂斯的桃花裝飾自己。
陳義芝溯目的是一川不敢瞻望的歲月,映著一圓咯血的夕照。
洪醒夫那年秋天的兒歌,往往只唱開頭幾句,便不能把它唱完。
而我,茫茫然,牽著白馬與河同悲。
掌杉說:我們原是不該成長的足跡,出現於未舉步的遠方。
瘂弦的詩作「歌」寫著:
誰在遠方哭泣呀
為什麼那麼傷心呀
騎上白馬看看去
那是戀
是的,我們戀著詩。我們堅持騎著白馬。
後來,我們在那個時代,真是詩壇的「後浪」。
誰不喊著:後浪來了!
浪花在台灣中部的西海岸沙灘上寫下匹匹白馬涉水的蹄印。
那是一九七0年代的事了。
3
我在一九七0年代的流浪意念一直延續下去;詩,變成我的鄉愁。
精神上,我是一名憂鬱的異鄉人。
柳川岸上的柳枝和我額際的髮絲拂去我那段蒼茫的日子。
我行,隨著存在主義的思想散步。
我寡言內歛,白馬卻代我嘶鳴。
北方詩人國度的周夢蝶聽到了,我最最生命底層的聲音。
蕭蕭如風,催我舉步出發。
我背起行囊策馬馳向龍族。
回首,才知我在和自己的影子競賽,向著光,我永遠超前。
回首,才知我的影子停留在本土哀嚎。
我倦怠地放下手中的繩索,只是白馬不願離去。
4
再上大肚山,西望台灣海峽,我終於落腳,求生。
生活是苦悶,所以藉由詩來抒發。
相思林的黃色花穗和鳳凰木的紅色花瓣依然燦爛。
我的白馬又自在的活著,召喚著我再度去擁抱牠。
然後,我捨下功名爵祿的冀望及學業的深造,純粹生活和寫詩。
無非我的內向個性使然,淡泊無為。
我不慣於向外放射,只是安於向內凝視。
我吸納著光,而不是映照著光。
所以近在周圍的人感覺不到我的存在,還因為:他們不寫詩。
只要暗夜形成,我坐於孤獨的位置,掌燈。
羅門以他的靈視看見了燈裡的我,包在燈罩裡的一個渺小的火焰。
白馬在暗夜的星空飛翔,以想像的翅膀,拍擊我的夢。
那是一個不斷重複的夢,接近黎明,卻盡速陷落於黃昏的籠罩下。
我被夢的使者帶走。
5
想起獨釣寒江的林興華失渡時,合十,膜拜自己。
想起李仙生在我驀然回首時,他那溫暖的影子依舊微笑著。
想起東海的李勤岸或牧尹,他說樹的哲學是在發表翻新的語言。
想起許茂昌的誓言:「當我倒下,請用一千首詩把我埋葬。」
我實在不忍,不忍詩人會在時間裡絕版。
許多個日子以來,總在思索曾騎著白馬的同伴往何處去了。
詩,會是青春的遺產嗎?白馬,會離開青春嗎?
遺忘已經開始,傷口忘記了執刀的那隻右手。
結成疤的,也許有一天都一一還原為血和痛。
二十一世紀的詩人怎麼看待我們現在這一代?
我們怎麼走下去?涉水無聲,踩泥無跡,蹄過無痕?
這些問題在詩史上只變作一兩個註解罷了。
就像一兩滴眼淚,何必在乎!
6
到了一九九0年代,詩,仍然是我唯一的鄉愁。
在這座現代詩的島嶼上,鄉土是我的畫面。
但我堅持從內裡寫起,不單單只寫外表;而寫內裡必寫到最深處。
因此,看見我多麼的超現實,而看不見我多麼的鄉土。
詩之所以為詩,不在於內容是什麼,不在於技巧有什麼。
詩,在於它自身的存在位置,是否能建築於人的心靈裡。
我逐漸有一些些體認時,歲月恍惚已過二十數年。
此刻,我又懷念起楊喚「童話王國」裡騎著白馬的小弟弟。
我撫著詩稿,喃喃唸誦著瘂弦的詩作「歌」:
誰在遠方哭泣呀,
為什麼那麼傷心呀,
騎上白馬看看去,那是戀。
那是戀嗎?戀著年少青春,戀著昔日寫詩的伙伴,戀著那場約定。
既是戀,亦即宣告:心願未了。我,我們,還沒完成的詩篇。
何不相約騎上白馬看看去?看台中盆地,看大肚山,看西海岸。
看看誰在遠方哭泣,是未舉步的,另一匹白馬嗎?
是我們永遠的鄉愁嗎?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寫於大肚山麓
註:本文為詩集《我牽著一匹白馬》之序
全站熱搜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